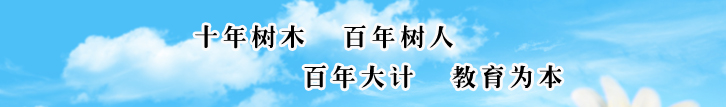出国
人生几十年,其中总会有一件或几件事给其一生带来一些比较大、甚至是转折性的变化,乃至改变生命轨迹。而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事,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初我被国家公派出国进修的经历。
1980年3月,我作为两国外交部之间的留学生交换项目学生被派到澳大利亚进修。该项目始于1979年,第一批公派人员包括北京大学的胡壮麟、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胡文仲、华东师范大学的黄源深、西安外国语学院(现西安外国语大学)的杜瑞清、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侯维瑞等9名高校教师,他们这一批被派往悉尼大学。我们这一批总共8人,被派往地处墨尔本的拉筹伯大学,其中高校教师5人,我是其中之一。
记得是在1979年冬天,有一天我没有课,没去学校。午饭时分,我接到电话,叫我回电英语系总支办公室,找姓曹的老师。我不敢怠慢,马上回了电话,接电话的是总支副书记曹萃亭,他说有一个到澳大利亚进修的名额,学校决定给我,让我下午去学校了解有关细节。
等我再端起饭碗时,手都在发抖,我妈问我怎么这么冷。其实我是紧张,是兴奋。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那个年代被派出去的人很少,出国进修这种好事怎么会轮到我呢?时至今日我依然不知道是谁作出了这个影响我一生的决定,无论是谁,我都永远心存感激。
留学生活
1980年3月,我开始了在拉筹伯大学的留学生活。出国前,我唯一能做的准备就是把当时英语系教师阅览室里绝无仅有的一本原版语言学方面的著作——英国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的Cohesion in English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们是第一批公派到墨尔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澳方学校对我们这批中国学生一无所知,他们感到陌生和好奇,但十分友好。澳大利亚的大学实行的是一年三学期制,第一学期我们被安排到语言中心上课。
毫无疑问,我们都以优异的成绩从语言中心毕业。此时,从悉尼传来一个消息:在悉尼大学进修的学长们开始攻读硕士学位了。这对我们是一个触动。研究生教育当时在中国几乎是个空白,尤其是文科专业。经过一番商议,我们5个高校教师中的4个向校方提出读硕士的请求。记得我们4人一起去面见教务长时,他指着几本厚厚的、用硬皮封面精装的论文问我们:“你们能写出这样的论文吗?”说实话,那个年月,出国前我们谁都没有做过真正的科研,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于是校方提出要我们先在导师的指导下读一个学期的预科,看看我们能否完成作业,是否具备读硕士的条件。
鉴于我们4人的特殊情况,校方专门给我们指定了一位导师——来自该校教育学院的高级讲师玛塔·雷多博士。她20世纪30年代从匈牙利移民到澳大利亚,是一位哲学博士,到澳大利亚后才转向教育学和语言学专业,主要方向是双语教育。
第一次见导师,不知如何称呼,她对我们说:“就叫我玛塔吧。”
玛塔的年龄大概在60-65岁之间,是个很要强的女性,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投入。我经常听她说的一个词就是update,也就是不断更新知识,跟上发展。她每天都要浏览各种学术期刊,并且做卡片(那时电脑还没有普遍使用),有时也让我们帮她做,以供日后查阅或推荐给学生。由此我感觉,要做一个合格的导师,要在学术界立足,靠吃老本是绝对不行的。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做一个合格的导师,是要终生不断作出努力、不断提高、不断自我完善的。
至于语言学方面上什么课,玛塔征求过我们的意见。那时我们对语言学这个领域知之甚少,作为教师,我们只想学一点和教学关系密切的语言学,而不是那些过于深奥、抽象的语言学。玛塔便根据我们的要求,指导我们在语言功能、语义、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交际等方向去研读。由于我们的特殊背景,玛塔的上课方式也很灵活。她并不把自己限制在某某学科的范围里讲课,而是根据授课过程中我们的反应、发现的问题随时修订授课内容。为了让学生最大程度上获益,可以暂时放弃系统性,先把有关知识讲授给学生,然后再形成系统。而形成系统的工作完全可以留给学生自己去做。她称此为“拼盘方式”。所以,实际上她并没有把教学限定在几门课程内,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融合多个领域、多个方向的“大拼盘”。
刚开始上她的课,我们这些习惯了老师把一二三都讲得很清楚的学生,实在是不适应。她从来不会在我们的小班课上把某一个内容讲得很全面、很透彻,而往往只列要点、勾框架,接着就让我们大家提问题一起讨论。每次上课玛塔都会布置课后的文献阅读,她把有关文章介绍给我们,还鼓励大家到图书馆去找更多的文献。这其实就是研究生应有的学习方式。我们这些习惯了填鸭式教学方法的“教师学生”(teacher-student)到这时终于醒悟了。
有人问过我:“你的语用学是不是在澳大利亚进修时学的?”其实玛塔当年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语用学这门课,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语用学对中国高校来说绝对是一个陌生词,国外大学系统开设这门课的也属凤毛麟角。但玛塔可以说是我语用学的启蒙老师。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最早是如何接触到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那天下午是玛塔的课,她身着宽大的裙服,脚蹬高跟鞋,一手拿书,一手拿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locutionary、illocutionary、perlocutionary(言内行为、言外行为、言后行为)3个术语。她作了很简单的解释,我们都没怎么听懂,她大概也没有期待我们一下子就能懂,就让我们到图书馆去找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如何以言行事》)这本书。我就是这样被她推进了这扇门。有时我想,汉语里把指导研究生的老师称为“导师”,以有别于一般的“教师”,我觉得这个称呼很好,到了研究生学习阶段,学生更需要的是被“导”,而不是被“教”。导师在课上给学生讲课只是一个方面,在研究生阶段,更重要的是学生的自主学习。
玛塔的课基本上隔周一次,每次上完课后都会布置阅读,到下一周见面时,就要有一名同学作汇报,然后大家讨论。当然我们的阅读并不限于她推荐的几篇文章,还会自己到图书馆去找更多的资料,觉得有价值的就拿到讨论会上来。其中也不乏导师没有看过的,但她不会因此而感到尴尬,反而会表扬、感谢推荐好文章的学生。导师和研究生既是师生关系,也是一种同仁关系。导师指导学生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提高的过程。
很快就到了最后的写论文阶段,我们4个人中有两个(包括我)选择了语言方向,另两个选了文学方向。选语言方向的由玛塔指导。首先是定题,玛塔从不指定题目,写什么由学生自己决定,但她会和你讨论题目的可行性。她说:“你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定题,尽可能选我不熟悉的题目,如果你们写的内容我都知道,那你的论文还有什么价值呢?”此话初听有些荒谬,导师怎么能指导学生写自己不熟悉的题目呢?但细想一下也有道理,导师的作用是指导学生怎么写,如果学生能把导师原本不懂的东西,写到让其能看懂,这一定是一篇成功的论文。如果都是导师熟悉的内容,学术研究还能有进步吗?玛塔对我们两个中国学生的论文指导很用心,她要求我们每完成一部分就给她看一部分,而且是一对一、面对面地讨论、指导、逐字逐句修改。我还记得在她办公室和她讨论论文的情景,时间大多是晚饭前的五六点钟,她会备好葡萄、苏打饼干、奶酪、橄榄之类的食品,边谈边吃,其实那是她部分的晚餐。虽然她的英语完全没问题,但有一次遇到了一个语言表达上的小疑问,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她居然说:“这个问题最好请教一下母语使用者。”可见她在学术上的严谨,以及对我们的负责。
如今我国的研究生制度已经十分成熟,而我所处时代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还是一个空白,我有幸到国外去攻读学位,亲历读研的全过程,对我回国后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回国后不久就开始招收硕士生,1995年开始招收博士生,我当年的学生如果看到这篇文章,一定会恍然大悟,原来何老师指导我们的方法,都是从他的导师那里学来的!
回国
20世纪80年代,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整体工作氛围很好。从校领导到教师都热情高涨,人人都想尽快让教学走上正轨,重振上外在外语教学界的雄风。回到学校,我感觉人人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既为学校,也为自己奋力工作,每个人都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同事之间没有太多竞争和攀比,更多的是自我比较。为数不多的刚从国外进修回来的教师无疑比其他人具备更好的条件,具有更宽阔的施展才能的空间,自身的责任感也更强一些。
回国后,我立即被安排上三年级的精读课。出国前我一直教一、二年级的基础课,教三年级的精读无疑是一个跳跃,困难也不小。不过凭着自己扎实的英语基础,以及留学经历带给我的开阔眼界,我很好地胜任了这个工作,深受学生的欢迎和好评。三年级我一连教了9年,直到1991年底我去美国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
我认为,青年教师上低年级的基础课非常有必要,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磨炼的机会。后来我担任英语学院院长时就规定,凡是留校的青年教师,一律从一年级的精读课开始教起,经过几年的磨炼后再根据个人特长考虑教授其他课程。
回国后我做的最有意义的两件事是在上外英语系开设了两门课,并编写、出版了两本相关教材。一门是给本科生开设的语言学课程。20世纪80年代,高校外语专业用外语给学生开设语言学课程的几乎没有。当时系里刚从国外回来的青年教师共有3名,戴炜栋(留学新西兰)、华钧(留学英国)和我。我们3人在国外学的都是语言学,大家一商议,都觉得外语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一定的语言学知识,近几十年西方语言学研究硕果累累,何不把我们学到的一点语言学知识凑成一门课呢?3人一拍即合,于是上外英语系的课程表上就增加了一门新课——简明英语语言学,旨在给英语专业的学生介绍语言学各主要研究领域的基础知识,包括基础理论、发展历史、主要原则、研究方法、应用价值,等等。
我们开这门课时手头没有现成教材,国外出版的语言学导论类的教材不少,但都不适合给中国学生用。于是,我们边上课边编著教材,参考的是我们从国外带回来的资料和教科书,根据中国学生的英语程度和接受能力编写。最终,我们3人合作编写了《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一书,于1984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年经修订后更名为《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2010年又出了第二版。这本适用于英语专业本科生开设学期课程的教材,因其内容覆盖较为全面、语言简明、难度适中,符合本科学生的实际水平而被全国许多院校的师生所接受。从1984年问世到现在,总印数已超过100万册,对高校英语专业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的作用不言而喻。
另一门课是给硕士研究生开设的语用学课程。我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并没有上过语用学这门课,我是受到玛塔的启蒙之后,自己研读有关文献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语用学的范围有多大,包括哪些内容,当时还不是很清楚,哪怕是现在,语用学也不是一个边界很明晰的学科。但在当时,我至少可以判断哪些能算作语用研究的内容。我认为,对语言研究做最粗的分类,可以分成对语言本体的研究和对语言使用的研究。我感兴趣的是后者,感觉在这个范畴我或许能够做一些深入的研究。解释语言使用的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莱斯会话合作原则,当时对国内的研究生来说都是陌生的。于是我便有了给硕士生开设这门课、做点引介工作的想法,就用当初我的导师把我引进门的办法,也把我的学生引进语言研究这块领域。
1986年,我给上外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开设了语用学这门课,现成的教材肯定没有,我把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积累的文献资料让学生拿去复印后作为教材,上课以我讲解为主,但是我已经开始注重学生的参与,要求研读文献、课堂讨论。
我的《语用学概要》一书于1989年出版,比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广州外国语大学)何自然老师的《语用学概论》晚了一年。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比较全面的介绍这一新兴学科的专著,我国的研究人员和语言专业的学生可参考的文献资料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下,不论是上外的“概要”还是广外的“概论”,都起到了把国外语用研究的主要成果向国内引介的作用,对于推动我国语用学的教学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89年出版的《语用学概要》只有七章,10年后,在我的3位博士生(俞东明、洪岗、王建华)的协助下,《语用学概要》被拓展、更新为包含十章的《新编语用学概要》。由于很多院校的语用学课程是用英语开设的,不少同仁建议我们用英语编写一本类似教材,于是2011年,我们又出版了Pragmatics一书。
我对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并没有因为时间久远而模糊,因为那个时期的记忆和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那个时期的学习、工作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获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91年12月赴美国俄勒冈大学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