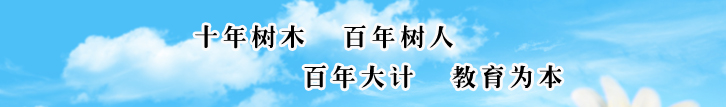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朗斯特罗默
靠狗和信鸽般的神秘罗盘“回家”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和诗人们在一起。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1931年生于斯德哥尔摩,是公认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1954年发表处女诗集《17首诗》,先后出版《途中的秘密》、《半完成的天空》、《看见黑暗》、《小路》、《为生者和死者》、《悲哀贡多拉》等诗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生活简单,从斯德哥尔摩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后,一直边写诗,边在社会福利机构担当心理咨询员。
■张杰
日前,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向媒体公布,80岁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获得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托马斯获奖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争议,诗人靠实力“把诺贝尔文学奖带回瑞典”。尽管托马斯只写过200多首诗歌,却让国际诗坛为之震撼和心服口服。连曾获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裔美籍诗歌巨匠约瑟夫·布罗茨基,都恭敬地承认自己的某些诗歌意象是从托马斯那儿“偷”来的。
诺贝尔委员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通过凝炼、透彻的意象,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真实的新途径。”此前,托马斯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曾表示,“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默,尽管他是瑞典人”。
诗人记忆中的托马斯
托马斯和中国颇有些缘分,曾两次来过中国,两度获得中国诗歌界颁发的诗歌奖,并和北岛、李之义和李笠等多位中国诗人、翻译家成为朋友。他还曾为中国写过短诗,随着他的获奖,那首短诗《上海的街》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2001年,参加李笠译《特朗斯特罗默诗全集》出版活动的托马斯第二次来到中国,中国诗人蓝蓝错过了和他的相见。2009年8月,蓝蓝和诗人王家新、赵野、沈奇应邀到瑞典参加“瑞典歌特兰国际诗歌节”,在斯德哥尔摩由李笠带领去托马斯家做客时,她见到了这位仰慕已久的诗人。蓝蓝发现托马斯家里挂着两幅中国书法作品,在客厅里的那幅被挂反了。李笠称挂在客厅里的那幅行书是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一位书法家的作品,而书房里的篆书则是李笠的一位旅居瑞典的书画家朋友去看托马斯时带去的礼物。
一周之后,李笠夫妇于瑞典家中宴请托马斯夫妇和一些瑞典诗人。两次相见,第一次蓝蓝唱了一首哈萨克民歌,王家新唱了一曲《兰花花》,沈奇唱了一曲《信天游》。托马斯兴奋之余,用左手为中国诗人们弹了一首俄罗斯作曲家格利埃尔专门为他写的单手钢琴曲,并向他们赠送有着诗人缓慢签名的诗集。第二次见面蓝蓝朗诵了托马斯的诗《巴特隆达的夜莺》:“夜莺北侧的绿色午夜/沉重的树叶痴迷地挂着……时间从太阳和月亮那里汹涌直下/流入滴答作响的同样的钟表/但这里并没有时间/只有夜莺的婉转/那朴素悠扬的歌声磨着夜空明亮的镰刀。”那次瑞典之旅后,蓝蓝写了一首献给托马斯的诗——《特朗斯特罗默在弹琴》,王家新则写了一首叫做《特朗斯特罗默》的诗。
中国诗人理解的托马斯
20世纪90年代,蓝蓝在《世界文学》杂志上看到托马斯的几首诗歌,以后陆续读到北岛、李笠和董继平的翻译。蓝蓝称托马斯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有一种间接的影响,主要包括观察事物的视角、处理生活细节的方法等。蓝蓝表示自己喜欢托马斯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在诗歌表达上的极其克制、冷峻和迂回曲折。蓝蓝认为任何诗人都是一团火,只不过有的火苗是黄色的,有的是蓝色的,人们对托马斯的误解在于因其表达上的克制,忽略了情感的浓烈和炽热。诗歌就是诗人的脸,诗人在诗歌中是不会撒谎的。
听到托马斯获奖的消息,当时在韩国首尔参加文学活动的王家新说自己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喜悦。
王家新和其他诗人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接触托马斯的诗歌并被深深吸引。当时在《诗刊》工作的王家新看到的主要是李笠的译本,后来在编选《欧美当代诗选》时,王家新也选了李笠翻译的托马斯的诗歌,并且催促李笠制订翻译托马斯诗歌全集的计划。受李笠邀请,王家新为该译本写了一篇叫做《取道斯德哥尔摩》的文章作为跋,谈论托马斯的诗歌特点及其翻译问题。他表示读托马斯的诗会产生一种很深刻的认同,托马斯是自己想成为的那种诗人,与他有一种可以同呼吸共命运的诗人家族感。
诗人、青年翻译家赵四手上正在编辑李之义翻译的托马斯的最后一本诗集《巨谜》。《巨谜》是托马斯中风后所写的一本短诗集。赵四认为在托马斯诗歌的中译者中,李之义的译本不容忽视,是托马斯最好的翻译家之一。李之义说,有一次托马斯专门为李之义弹了一段钢琴,以说明其诗歌和音乐的节奏与结构相类似,称其为一个像谱曲一样写诗的诗人。
李笠则认为,托马斯的诗有点像唐朝诗人王维的诗,“但他是一种对后工业社会的直观感受,王维的‘鸟鸣山更幽’的意境,在特朗斯特罗默的诗中也有,但他写的是‘直升机嗡嗡的声音让大地宁静’,这种力度是前者无法比拟的”。
■文化观察
用蜗牛的速度登临峰巅
■金星
一个人在23岁的时候出版处女诗集《17首诗》,然后每隔4到5年再出一本诗集,而每本诗集的容量一般都不超过20首诗,如《途中的秘密》和《半完成的天空》等。有诗评家给他算过,他平均一年才写2到3首诗。一直写到第200余首诗的时候,已是80岁高龄的他终于获得了20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就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形容他的作品“简练、细腻,充满深刻的隐喻”。而看国内媒体近来对特朗斯特罗默的报道,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提到这位大诗人仅写了200余首诗这一事实。显然,这不是在极言其创作速度和创作数量的快而多,而是在叹服其慢而少,并因此而奇迹般地取得了他人难以匹敌的艺术成就。
想必当下正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在由衷地叹服特朗斯特罗默这个瑞典老头,因为,已很少再有人能像他那样把诗写得如此精炼、精确、精妙与精彩。可首先要知道的是,他写得简直比蜗牛爬行还要慢,他的诗一般要花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算完成,其中长诗《画廊》用了10年,而短诗《有太阳的风景》从手稿到发表竟是历经了7年。他自己也曾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完成一首诗需要很长的时间。诗不是表达‘瞬间情绪’就完了!”不妨想象一下,这“瞬间”之后,他又是如何的专注与沉思。而最终,他又总能把激烈的情感寄寓在平静的文字里,使作品在瞬间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少而达到了极致,因慢(他在许多年前就已拄起了拐杖)而登临了峰巅,但又是那样的令人击节赞叹。由岁月之花集成的桂冠,也只有这样的人才配顶戴。
特朗斯特罗默来过中国两次,在谈及因游历而激发的创作时,他曾这样揶揄可能同属他一个国度的某位著述丰富的作家:“他去中国一个月,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而谈到自己时,他则说:“我要是在中国生活三年,也许会写一首诗。”幸亏他这次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首就一首吧,大可以一当十,否则,我们肯定是要大为抱憾的,因为我们实在是一个越来越讲求快而多的国家。单是他这区区200余首诗,我们的随便哪一位诗人只需一年乃至半载就可轻松“搞掂”。而诗歌之外,更是“短篇不隔日,中篇不过周,长篇不逾月”,真的是到了如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所说的那样,“请试万言,倚马可待”。同道相遇,问的不再是“你近来在思考些什么”,而铁定是“你今天码了多少字”。以快手自傲,以数字称雄,文字圈中,显然是少了苦心孤诣,多了轻狂放任。自然,创作速度快也不一定不好,但粗制滥造及眼下越来越为读者所厌憎的粗鄙化倾向,无疑都与过快过多大有关联。近来,作家毕飞宇因《推拿》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他在获奖感言中也讲到了静悟与淡定的重要,讲到了对节制的尊重。但在普遍追求快而多的情势下,他的声音显然是那样的微弱并难以由己及人。
从国内媒体对特朗斯特罗默的报道,我们不仅知道他曾两次来过中国,而且在2011年4月23日的广州,我们还把民间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诗歌与人·诗人奖”授予了他,可见我国的诗人对他并不陌生。只不过那一次他人没到,但写来的答谢词依然是那样的睿智和精妙,其中云:“诗歌是禅坐,不是为了催眠,而是为了唤醒。”但愿,写得少一点,写得好一点,对每一首诗或每一篇作品都多花些时间,就当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我们的诗人、作家们的“唤醒”之一吧。
|
■致敬
特朗斯特罗默在弹琴 ■蓝蓝 文/摄 特朗斯特罗默在弹琴 用他的左手。 一道山岗上有午后的书房 格利埃尔的谱子,风中的 白桦林齐刷刷站立在 梅拉伦湖畔的房屋,等待 一只手收回它们风中的落叶 那些已知的痛苦和未来的悲伤。 他微微闭上眼睛 手指下蔓延着风和波浪 窗台上的天竺葵突然一片火红! 人们认为所有重要的事情 都可以用右手来做。失败, 这是他想要的抵达—— 特朗斯特罗默在弹琴,用他 老人的左手。
|
雕之峭壁
养殖场玻璃后面
爬行动物
惊奇地一动不动。
一个女人横挂在
寂静之中。
死者无声。
大地深处
我的灵魂滑动
无声无息像一颗彗星。
雪飘
接近一座城市,
坟墓
越来越密,
像是路标。
长长阴影的国度里
千万人的目光。
一座桥正在自建
慢慢地
直指苍穹。
(李之义 译)
四月与沉默
春天荒凉的存在
天鹅绒般发黑的水沟
在我身边爬动
没有反影
那唯一闪耀的东西
是黄色的花朵
我被携带与我的影子中
像一把被携带在
黑色琴匣中的小提琴
我要说的唯一的东西
闪耀在无法企及之处
就像当铺中的
白银一样
半完成的天空
懦弱中断自己的行程
恐惧中断自己的行程
兀鹰中断自己的翱翔
急切的光迸溅而出
连鬼魂也品尝了一口
我们的画出现在白昼
我们冰川时期画室的红色的野兽
一切开始环视
我们成群结队地走入阳光
每个人都是半开着的门
通往一间共有的房屋
无垠的大地在我们的脚下
水在树林间闪烁
湖泊是对着地球的窗户
(李笠 译)
《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15日第4版